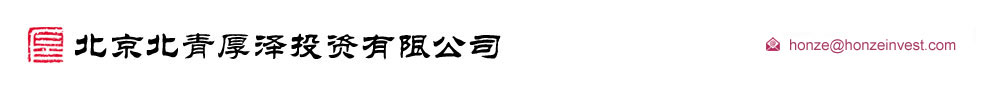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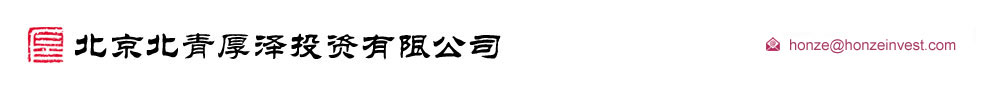
未來,北京老人應該選擇哪種方式安度晚年,是在社區就近養老,還是到河北異地養老?

8月2日,北京市朝陽區八里莊南里社區日間為老服務站正式掛牌成立,該服務站周一到周五9時至16時向社區內老人免費開放。
服務站96平方米,為社區內的老人們提供健康知識講座、基本健康咨詢等服務,中午每位老人支付12元,可得到一葷一素的餐食供應。
在北京,這樣的社區養老服務站被稱為第三級驛站式養老,于2015年在朝陽區推廣,該區計劃在2016年再新建100家類似的社區養老服務機構。
此前,北京市民政局局長李萬鈞公開表示,北京不再新建大型的養老機構,今后將會把養老產業向周邊地區疏解。
2016年6月,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門舉行了第一次聯席養老會議,并簽署《京津冀養老工作協同發展合作協議》,這個協議的目標是破解異地養老的政策瓶頸。
同時,河北北部毗鄰北京的多個地區,包括涿州、高碑店、承德、張家口等地在內,大舉建設大型養老機構,以期搶占京津冀養老市場。
未來,北京老人應該選擇哪種方式安度晚年,是在社區就近養老,還是到河北異地養老?
養老供需錯配
八里莊南里轄區內人數7682人,60歲以上人員的數量2016人,占社區總人數的26%,是典型的老齡化社區。
該社區為原北京棉紡廠的職工宿舍,住戶多為棉紡廠退休職工,平均退休金為每月3000元左右。
除去為老服務站外,社區內還有一家康復醫院,專門接收失智、失能老人,月收費6000元至1萬元不等,該機構共有110張床位,已入住120名老人,另有數十名老人在排隊等候入住。
八里莊南里社區為老服務站就是這家康復醫院與六里屯街道辦事處合建的。
2015年,北京市民政局、規劃委提出“9064”養老服務發展計劃,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會化服務協助下通過家庭照顧養老,6%的老年人通過政府購買社區照顧服務養老,4%的老年人入住養老服務機構集中養老。
按照這一計劃,八里莊南里的120余名老人被歸入了“4%”的這部分人群。為老服務站的一名工作人員表示,政府對于社區內的養老驛站會給予最高80萬元的建筑、硬件設施補貼,但后續服務尚未給出補貼標準,目前服務站的人力成本均由康復醫院負擔。“受限于外部條件,這里提供的服務多是指導性的,如幫助老人識別老年用品,指導家人如何對失能老人進行護理,而非以長期照顧服務為主。”該工作人員表示。
一位北京醫院科研處人士說,北京老人的患病比例不斷上升,家庭結構的小型化導致老年人家庭照料人口不足,但政府的供給有限,供需矛盾較為突出。
截至目前,北京778家養老機構共提供了12.27萬張床位。58%分布在密云、延慶、房山等郊區及農村地區,這些養老機構受限于資金,管理、服務水平較低,入住率也不高,服務對象多限于農村地區的孤寡老人。
城六區內,養老機構則分為政府辦和社會辦兩種,其中政府辦養老機構服務好、價格低廉,但床位爆滿,如第一福利院、四季青養老院分別有1萬名和5000名老人在排隊等候入住,等待時間為數十年。
社會辦養老機構收費較高,目標人群主要為高收入的老年人群體。清華同衡養老產業專家委員會副秘書長張勁松認為,這類養老機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服務錯配,即養老機構提供的服務不能滿足老人們對醫療及日間照料的需求。“不少高端養老機構發展的實為養老地產,企業只是為自己的房地產項目找一個概念而已。”
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則認為,這類養老機構價格高,面向的是生活可以自理的老人,對在家無法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老人來說,不能滿足其剛性需求服務。所謂剛性需求,即因身體原因對機構養老需求迫切的老人。
與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2015年發布報告稱,北京的養老機構入住率僅為40%。
以昌平區金手杖老年養生公寓為例,其會員費為115萬至170萬元不等,提供康復旅游、健康食品、資產管理等服務,但沒有針對失智失能老人的護理服務。這種價格與服務內容決定了金手杖老年養生公寓及相似項目不可能成為托老首選。
此外,由于目前北京市可利用的土地資源有限,產業結構正在調整。養老產業也被列為疏解對象,占據地利之便的河北便抓住機會。
在與通州僅有一河之隔的燕郊,燕達金色年華健康養護中心的二期工程、8000張養老床位的建設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常務副總經理崔凱非常自信,“床位肯定能住滿”。
河北瞄準北京“三高”老人
燕達金色年華健康養護中心的建設初衷即為吸引北京的老人來養老。目前已投入使用的一期工程中包含507套面向生活完全可以自理的老人的公寓,1100張面向非自理老人的床位。
自理區已住滿,非自理區入住率達到95%,入住的老人中98%來自北京。
78歲的高天華退休前為新華社的一名行政人員,退休金為每月1萬元左右,他已經在金色年華健康養護中心住了兩年,養護中心吸引他的主要是環境及服務,“這里緊鄰潮白河,空氣比較好,而且社區內設有醫療站,如遇緊急情況,可以得到及時救助,甚至可以得到24小時的照料。”
相對優越的環境及服務背后,同樣是相對較高的入住門檻。燕達金色年華健康養護中心的一份收費價格表顯示,在自理區,每月收費從5200元至11500元不等,非自理區的價格則為每月6800元至14000元不等,特護則為每月11800元至17200元。
作為以盈利為目標的養老產業,崔凱稱金色年華的定位為中高端的養老機構,他說,發展高端產品有望在40年至45年內收回成本,如果大規模建設中低端的養老機構的話,成本回收會非常困難。
燕達金色年華健康養護中心建于2006年,建設初期河北省政府給予其80余萬元的建筑補貼,此后因為養護中心接收的多為北京老人,河北省未再給予每人每月50元至100元的運營補貼。同時,因地處河北,北京市政府同樣未給予其運營補貼。
三地簽署《京津冀養老工作協同發展合作協議》后,這一狀況有所改變,按照協議規定,自6月21日起,北京市政府將給予其自理老人每人每月300元、非自理老人每人每月500元的運營補貼。這家養護中心已被列為京津冀養老一體化示范基地。
養老產業占地面積大、經濟回報率低,但河北的積極性很高。目前,河北承德、張家口都意在打造“候鳥式”養老產業,涿州、高碑店則欲抓住京津冀協同養老的政策紅利推進養老地產建設。
“養老服務業有一條非常長的產業鏈,包括康復設施、老年金融、老年家居用品等。”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袁牧說,養老服務只是產業中的一部分,但服務的發展可以帶動周邊一系列的產業發展。
燕達金色年華健康養護中心的未來規劃也是這個方向。其二期工程預計2018年底投入使用,屆時將容納1萬余名老人。崔凱計劃發展保健品及老年旅游等后續產業及服務,并寄望它成為今后主要的盈利模式。
在燕達集團管理層的預想中,還希望推動醫養結合,把毗鄰養護中心的近幾年運營狀況不佳的燕達國際醫院拉入正常的運營軌道。這家醫院也將享受到京津冀協同養老的政策紅利。三地合作的協議中,將它列為河北省唯一一家完成與北京醫保政策對接的醫院,實現河北與北京的醫保政策在小范圍內互聯互通的突破。
目前河北養老產業瞄準的是來自北京的“三高”老人:高學歷、高收入、高齡。
社區養老應成主流
至2015年底,北京市60歲以上的戶籍老人數量為315萬人,且平均每天凈增500余名,預計這座城市至2030年將達到重度老齡化。
在河北,目前投入運營且可為失智失能老人提供照料服務的大型養老機構僅有燕達金色年華健康養護中心一家,即使到2018年底,金色年華的二期工程投入使用,在最大程度上也僅能承載1萬名北京老人,其中非自理區的床位僅為3500張。
按照“9064”的發展計劃,北京需要借助機構進行養老的老年人數量高達31.5萬。如何滿足這么多老年人的養老需求呢?
在北京不再興建大型養老機構的背景下,社區就近養老的重要性凸顯。
按照北京市民政局的“養老照料中心三年行動計劃”規劃,2016年將建成208個街道級養老照料中心。但現有的養老照料中心均因缺少資金還面臨著人員短缺、設施簡陋、人員缺乏培訓等問題。
一家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員表示,照料中心能夠為老人做的服務主要就是血壓測量、午飯以及提供場所讓老人進行以打牌為主的休閑活動,并不能滿足一些半自理老人的日常照料需求。
杜鵬認為,政府應投入資金對社區內的設施改造升級,打造成多功能的日間照料中心,“國外成功的案例建設的都是功能齊全的小型機構”。
較早進入老齡化時代的英法等國采用的多是社區照顧的模式,且具備完善的補貼機制。
英國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重點推行社區化養老模式,社區內建立老年公寓、暫托所、老人院等,分別滿足社區內有生活自理能力但無人照顧的老年人、家庭成員無法長期照顧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又無家庭照顧的老人的養老需求。
社區養老設施的建設、維護及工作人員聘請等費用,均由地方政府出資,同時社區還與醫療機構相結合,專門配備老年人健康訪問員,負責并探視各個社區的老年人。
與中國文化接近且老齡化問題嚴重的日本,主推的同樣為“小規模多機能”的社區養老。日本建設在居民住宅區小規模的老人中心不斷增多,這種社區型日托式老人中心均按照政府統一頒布的標準運營,標準細化到養老院建筑設計、護理服務等多方面。
而在人口老齡化速度快、老年福利支出大和社會負擔重的香港,政府資金無法全面的覆蓋養老服務,對“民間提供服務,政府輔助施行”的共同負責的伙伴關系進行了探索,如提供地區和鄰舍層面的社區支援服務的長者中心服務。
香港福利署還為老年人提供改善家居和社區照顧服務,2000年起推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社會福利署2003年開始設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集中為老人處理長期護理服務的申請和服務編配。
這兩種制度的出臺,保障了香港龐大的老年人群體在服務時間和服務內容方面的不同需求。